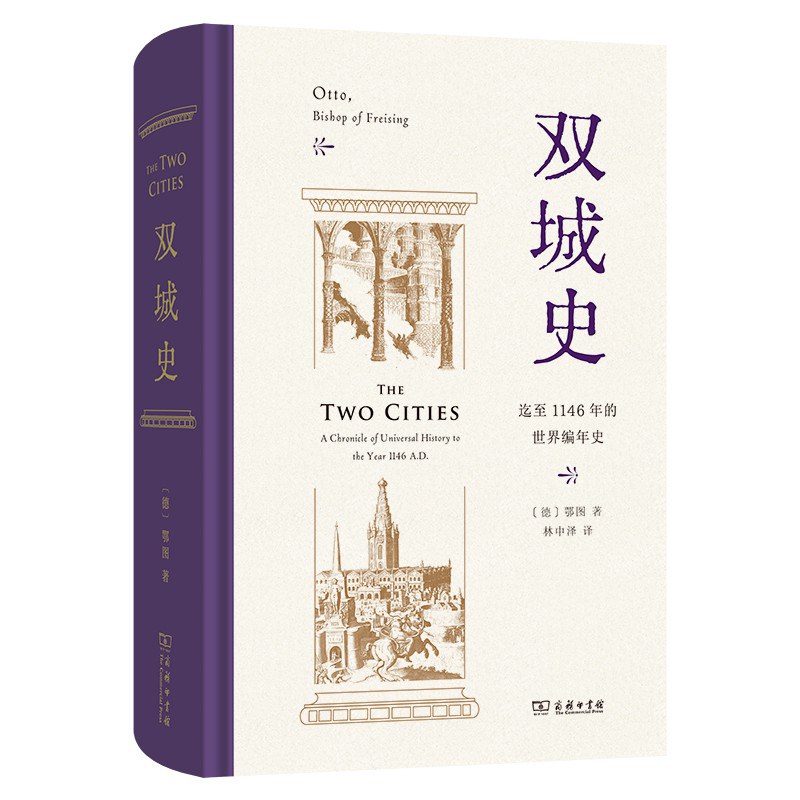
《双城史》,[德]鄂图著,林中泽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9月即将上市
弗赖辛主教鄂图( 约1114-1158年)的《双城史》,是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用哲学的方式对人类历史作理论说明和系统解释的作品,因此历来被看做历史哲学的肇始。该作品对此后西方学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启蒙运动之前的神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均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从它那里获取资源和灵感,并引用其中的段落或话语作为自身立论的权威性理据。由于其独特的学术地位,西方学界历来对之高度重视,研究作品层出不穷;可是它在我们国内却似乎仍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译作的刊出,便是为了对该遗憾稍作弥补,以唤起国内同仁对这一著名作品的兴趣,并达到助推进一步研究之目的。
诚然,“双城”的思想,最初源自于距鄂图七百多年前的早期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早就提出:上帝之城与俗世之城虽然是对立的,但后者并非一切皆坏,教会与国家并非截然相对抗;世俗国家也为上帝所需,教徒在俗务上应当服从它,与此同时,它也应当保护和帮助教会;但俗世之城或国家最后终将灭亡,并逐步由上帝之城所取代。由于奥氏是借助概述历史的发展进程去展开其对双城关系的分析的,故有人认为应当视其《上帝之城》为一部最早的历史哲学作品。可是,奥氏的整个叙述过程完全充斥着神学的意涵,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驳斥当时十分流行的基督教亡国论,并论证上帝意志对历史、现状,尤其是未来人类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为了通过系统的历史叙述去总结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之必然性和规律性,因此,奥氏的《上帝之城》虽然具有了历史哲学的雏形,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体系,则无疑是鄂图开创的。
对于奥古斯丁上述有关双城的基本理论和观点,鄂图在大体上是予以肯定并加以借用和继承的。不过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遭遇差异极大,两位作者的思想观念便不可能有很大的雷同,毋宁说,鄂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理论。首先,在奥古斯丁的时代(5世纪上半叶),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均处于外族入侵及内部动荡的双重压力之下,尤其是西部帝国更接近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基督徒)有理由相信世界末日很快就要到来,奥古斯丁便有理由预期俗世之城的瓦解和上帝之城的届临指日可待。而在鄂图的时代(12世纪初),人们不仅发现世界末日迟迟没有到来,而且看到世俗国家借助族群流动和政权变迁的方式,实现了统治权力的更新和延续,而且其尽头也似乎无法预期。因此,鄂图就必须对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做出新的解释。
其次,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基督教的合法性刚获承认不久,政教关系还相对简单;而且奥古斯丁本人出身于草根阶层,其与当时的各种世俗政权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因此,奥氏在处理政教关系问题上,就可以完全从纯理论的高度去加以尽情发挥。而鄂图的时代则不然。那个时候政教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加上鄂图本人既出身于皇族,又担任神职,是弗赖辛城的主教。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得不经常要小心翼翼地在皇帝与教皇之间尽可能取得平衡。据说他曾经亲自协调过自己的表侄皇帝腓特烈一世与教皇哈德良四世之间的争端,使二者重归于好。总而言之,在政教激烈争端的过程中,他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因此在其作品中,他的用辞虽然较为含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有时候指责皇帝的过分贪婪,有时候又贬斥教皇的过度野心。

鄂图的雕塑
《双城史》总共有8卷,其中第1—5卷是对前人同类作品的高度概括和综述;第6卷和第7卷比较系统和详尽地叙述了查理曼帝国分裂之后至作者时代为止,地中海区域的历史进程及复杂的政教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动,故特别具有创意和史学价值。在这当中,从第7卷的第12章开始至第8卷结束,所叙述的内容更是鄂图同时代的事件,这些事件不是他所亲身经历,就是得自于当时的一手信息,因此其价值尤其不菲。不过既然查理·克里斯托佛·米罗(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先生在其导论中已对之进行过颇为生动和具体的评述,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仅从历史的角度,对鄂图在该书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第一,鄂图认为,世俗势力亦即地上之城的兴起由弱到强,由强转衰,乃至最终走向毁灭,被上帝之城所取代。这一思想无疑是从奥古斯丁那里继承而来的,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帝国迁移”理论。在他看来,世俗政权以一种所谓“帝国迁移”的方式,从一个族群不断地转移到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族群手里;罗马帝国是最后一个而且是最为强大的世俗帝国,这一传统观念并没有改变,只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帝国的权力就逐渐转入了法兰克人的手里;在8—9世纪之交,随着拜占庭皇位为女皇艾琳(Irene, 797—802年在位)所窃据,以及查理曼(Charlemagne, 800—814年在位)在罗马的加冕,帝国的权力中心又从东部回归到了西部,故法兰克人的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如此一来,鄂图就为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找到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同时又没有减弱人们对于上帝之城的热切期盼。
第二,与“帝国迁移”理论相对应,鄂图认为人类的智慧起源于东方,然后逐渐向西方转移,并最后终结于西方。他明确告诉我们:
所有人类的力量或智慧虽然起源于东方,却开始在西方达到了其极限。……人类的力量……从巴比伦人传给了米底人和波斯人,又从波斯人传给了马其顿人,在那以后又传给了罗马人,接着又一次传给了罗马名义下的希腊人,……[最后]从希腊人手里转移给了居住于西方的法兰克人……(第5卷序言)
在具体叙述的过程中,鄂图无疑将中亚和巴比伦视作人类心智的最初发源地,并将由法兰克人为主体的神圣罗马帝国当成人类思想荟萃的最终场所。在他看来,琐罗亚斯德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心智的开始萌发,然后才有了亚伯拉罕和摩西等犹太人族长和先知,接着相继出现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及塞涅卡等异教智者,最后出现的是众使徒及基督教诸教父。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只限于对这些人类心智作简单的时间方面的排序,而是相信他们之存在着内在关联,亦即后来者对先在者存在着某种继承、发展和扬弃的关系;这一思想对于后来兴起的文明史观,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鄂图认为,罗马世界帝国的大一统,为基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和基础。他特别谈到屋大维元首体制的建立,使纷争了一百多年的罗马世界得以在一个单一政权的控制下获得了真正的统一,这种统一和随之而来的相对和平的局面的形成,不仅仅给人民的物质生活带来了福音,而且在造就人们的精神福音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亦即基督的降临和基督教的诞生。该观点之所以特别具有价值,就在于它把基督教的崛起放置在一个罗马世界历史转折的大背景之下,毫不讳言地主张罗马的统一及和平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和教会的事业,这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类似的看法,我们也可以在尤西比乌斯的作品中隐约地窥探得到,不过像鄂图如此公然为罗马元首制唱赞歌的例子,在此前的历史学家当中则较为罕见。
第四,尽管鄂图与中世纪其他神学家一样,对上帝之城的到来充满信心,可是他对于世俗事物的基本态度总体上是悲观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目睹了太多的时代磨难,尤其是政教争端。他理想中的政教关系本该是分工协作、互为表里及极其和谐的。可是往往事与愿违。皇帝与教皇的不断争吵,使他不胜其烦。加上他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经历,更加剧了其挫败感。因此,他对多数人的得救,似乎不抱太大的希望。到了末日审判的那一天,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能得救上天堂享永福?又有多大比例的人会遭诅咒下地狱受永罚?鄂图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众所周知,奥利金曾提出过“普救论”观点,认为一切人,甚至包括堕落天使亦即魔鬼在内,最后终究都要获救,可是该观点很快就受到了谴责。奥古斯丁则以预定论为依据,认为获救的不过是少数被特选的人口,而多数人口由于是上帝的弃民,是注定要受谴责的。考虑到奥古斯丁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对鄂图本人的深刻影响,再从鄂图的具体叙述去做出综合判断,比较可靠的结论应当是:他至少不是一位奥利金式的普救论者,而是一位“部分获救”论者。对于人性,鄂图也似乎不太乐观,他常常指责人的贪婪和野心是导致灾难丛生的根源。从他的这些指责中,我们基本可以初步推断:鄂图认为世上的恶比善更多,这与后来的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人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最后,我要重点提示的,是《双城史》的第8卷亦即最后一卷的相关内容。在这一卷中,对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做出了系统的描述。人的最终去处究竟会在哪里?这对于那些以形而上的高尚生活作为终生追求的上层人士或知识阶层而言,也许并非至关重要;可是对于一般的普通信众来说,则是利益攸关。故通过鄂图这一卷对来世生活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中世纪盛期基督教世界广大民众的信仰关切和愿景。虽然新约的《启示录》集中谈到了末日审判的情景,但其象征意味太浓厚,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是根本无法打动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读者的,因此鄂图的系统解释就显得非常必要。至少,鄂图用一种更加直白的方式,解释了《启示录》和《圣经》其他经卷当中有关第二次死亡、复活、审判、涤罪、地狱及天堂的具体情景及各个相关环节,并对其中的断环进行巧妙的拼接,对其中的相互矛盾之处进行得体的协调。他继承了长期以来在基督教世界中所流行的涤罪思想,给那些沾染有原罪但未曾犯过任何现罪的死亡婴儿,在地狱的入口处设置了一个洗涤原罪的处所;尽管该处所将随着审判的结束而最终消失,但它还是为此后不久兴起的“炼狱”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雏形和基础。
诚如米罗先生所说,鄂图是一位小心谨慎的和具有鉴别能力的杰出历史学家,其声誉获得了古代及现代学者们的一致好评,他的神学观在16世纪时甚至被承认为正统。他在写作体裁方面,继承了教会史之父尤西比乌斯所开创的世俗史与教会史并叙的套路,并有所发展,这就使他的作品不仅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撰述风格上,成为上接古代,下连近现代的承前启后的历史杰作。此外,该书文字流畅,词句优美,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优秀作品。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