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完全失聪后的贝多芬写出了音乐史上划时代的《第九交响曲》一样,约翰·弥尔顿在失明后的十多年间创作了长达一万多行的史诗杰作《失乐园》,一举成为比肩荷马、维吉尔、但丁的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然而,弥尔顿的天才与成就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位致力于争取人权和自由的思想战士,一位可以媲美博尔赫斯的阅读家,一位有着深厚音乐修养的骨灰级乐迷,一位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等八种文字的语言天才,一位热衷于出版各类“非法”小册子的散文家,一位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先驱,一位不顾失明风险的彻头彻尾的工作狂,“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雄辩家,最早提出“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并为离婚自由辩护之人……
回望弥尔顿离世至今的350年,其世界性的巨大影响力不断扩大与延展——从新闻出版到法律制度,从诗歌文学到影视艺术,从经济思想到社会思潮……卡尔·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说“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恩格斯将之誉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老前辈”,哈罗德·布鲁姆则断言“弥尔顿在经典中的地位是永久的”。即使是21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弥尔顿的伟大思想与艺术所参与建构的文明世界中。

约翰·弥尔顿肖像
英雄式撒旦
“我要创作一篇流传千古的史诗巨作。”25岁的弥尔顿曾在一封寄予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对于出身剑桥、少负天才的弥尔顿来说,这份自信其实由来已久。早在21岁时写下的《基督降生颂歌》中,他就大胆地把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诞生,与耶稣的诞生含蓄对比。渐渐地,这位不世出的少年天才毫无意外地成长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拉丁文学者之一,并曾试图重写《圣经》前几卷。然而,直到47岁双目完全失明后,弥尔顿才真正兑现自己25岁时曾抛出的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1655年,长篇叙事无韵诗《失乐园》由年迈的盲诗人开始构思和口授,并在整整十二年后问世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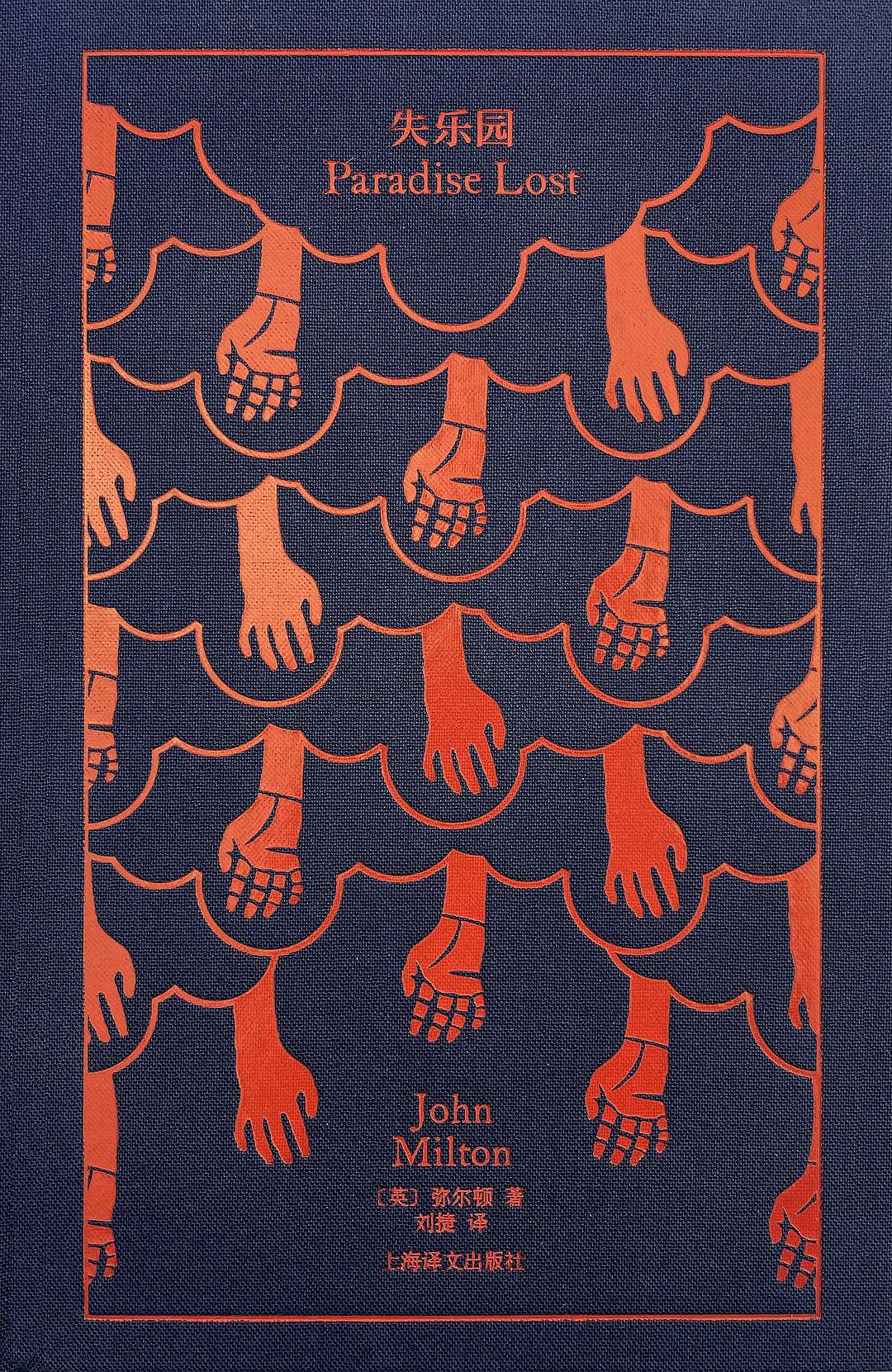
《失乐园》
这首在全然的黑暗与生命的暮年创作的“英雄之歌”,在语言、结构、思想等多个层面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最惊世骇俗之处,则是弥尔顿创造了一个对抗上帝专制统治的“英雄式撒旦”,一举颠覆了人们的常识性认知。是的,当我们打开这部由英文和拉丁文杂糅的诗篇,满心期待地想要读到关于亚当、夏娃以及伊甸园中苹果的故事时,弥尔顿却在一开始就把我们扔进地狱——我们看到反叛之神撒旦,因为反抗上帝的权威被打入地狱,却毫不屈服,后来为复仇寻至伊甸园。在开篇的26行里,弥尔顿就说明了自己的意图:他要“向世人昭示上帝之道的正当性”。于是,我们毫无防备地读到了这样的诗句:
想让我们卑躬屈膝来乞讨所谓的宽容,
将他的力量奉若神明,
而他不久前还被我们的大军吓得瑟瑟发抖,
以至他怀疑自己的帝国能否继续,
我们现在确实低下了头颅,如此的失败;
令我们蒙羞,乃我们的侮辱。
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失乐园》的读者来说,他们肯定做梦也想象不到,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讲竟来自我们常以恶魔形象指称的堕落天使——“撒旦”,而其口中“瑟瑟发抖”的“他”竟是上帝。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发明人性”的莎士比亚——在弥尔顿之前,只有莎翁把魔鬼的人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俯视群雄的高度。比如,《奥赛罗》的真正主角不是奥赛罗,而是其下属伊阿古。作为一个区区旗官,伊阿古竟能将身为威尼斯将军的奥赛罗、副将凯西奥、妻子苔丝狄蒙娜,以及一众威尼斯元老、官员绅士玩弄于股掌之间,只因他如魔鬼般洞悉人性,懂得如何利用丈夫对妻子的占有欲和男人对美色的贪婪。
犹如莎士比亚附体,弥尔顿创造性地改写了圣经旧约之《创世纪》,把撒旦描绘成口若悬河的雄辩家和超级推销员,单靠能言善辩和巧言令色,就能够逃出地狱、重返人间;并说服亚当与夏娃偷尝禁果,令人类从此堕落。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他的撒旦糅合了伊阿古的本体论虚无主义和麦克白的先期幻想,再加上哈姆莱特对妄言的蔑视”。在此,失败的魔鬼比无所不能的上帝更具说服力和诱惑力。此后,“魔鬼般的魅力”(devilish charm)一词登堂入室,成为英文的常用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更是直言:“最精彩的对白皆出自魔鬼的口中(The devil has all the good lines)。”这一由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开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时代人尽皆知的漫威电影中,《复仇者联盟》后两部最有看头的角色不是任何一个超级英雄,而是把超级英雄打到死去活来的大反派——掌握宇宙强权的灭霸,一个极具“魔鬼般魅力”的超级撒旦。
在弥尔顿的撒旦眼中,那些忠于上帝的天使们对上帝放低身段,屈膝承欢,并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可耻的。一个真正的全知全能的上帝,怎么会怀疑自己是否能驾驭他的王国呢?他的撒旦想要揭开的,正是由文化和宗教所塑造的高度戏剧化的上帝力量的幻象。不过,弥尔顿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作为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他当然无意藐视上帝,《失乐园》开篇的惊人之举实则暗含着他的政治抱负。要知道,弥尔顿一直都是坚定的议会派,他激烈反抗着保皇党,并扶持新共和国成立。通过洋洋洒洒的几百页反君主制宣言,弥尔顿助推了查尔斯一世的倒台。这几行诗句中,拒绝俯首称臣的撒旦像极了弥尔顿本人。接着,弥尔顿的撒旦喊出了最强音:
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倒不如在地狱里称王。
自由斗士
人类近代史上,1644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东西方两大重要国家——中国和英国在这一年开启了截然相反的近代史命运。甲申之年,明朝在内忧外患中彻底崩塌,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身亡,残明退守南京。满清王朝以“闭关锁国”政策故步自封,自绝于启蒙运动、工会革命等世界潮流之外。这一年,同样举步维艰的英国却上演了决定国运的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 of Marston Moor),克伦威尔率领由自耕农组成的“铁骑军”大败查理一世的国王军,议会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法案》,为不久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东西方两大强国正式交锋,最终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双方实力在过去两百年间的此消彼长不言而喻。
其实,我们还忽视了一条隐秘的暗线。依然是这个年份,弥尔顿在1644年写下了一本极为重要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正是这篇作品,为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作了最初辩护——他在文中主张思想市场(Market of Ideas)的崇高地位:“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试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论出版自由》与马斯顿荒原战役同等重要,前者就像是思想和制度领域中的一场风暴,引领了英国18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一词由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于1707年发明),成为推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而大清王朝,却是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严酷文字狱而著称于世,其历时之长、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惩处之酷,可谓前无古人,对科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几乎是毁灭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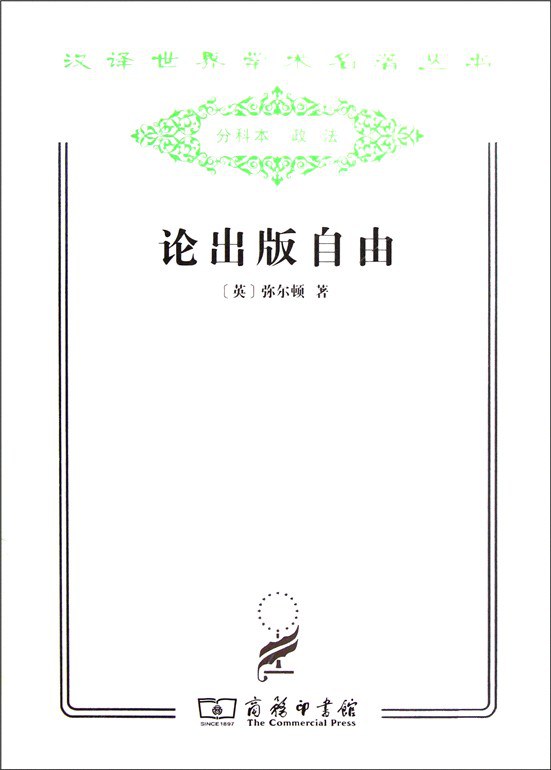
《论出版自由》
对此,20世纪法国重要思想家,雷蒙·阿隆曾不无艳羡地说道:“在英国,争论从本质上说是技术性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因为人们意识到不同价值是可共存的,而非相互矛盾的。”对知识分子和思想自由的宽容,成为英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巨大的无形优势,它极大地助推了英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谁都记得,流亡中的卡尔·马克思在伦敦找到了宁静的学术环境,得以从容书写他那志在毁灭寄居国制度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而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正是从书报检查对“人”的压迫角度,批判、质疑和否定了书报检查令,弥尔顿的影响不言而喻;伏尔泰、卢梭等法国启蒙群贤遭受迫害时,也纷纷在英国得到庇护;没有英国“光荣革命”的卓越示范和英国哲人洛克的《政府论》作指引,法国大革命也许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17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依然是一个保守而专制的国家,与后来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相去甚远。即使放眼全欧洲,宗教势力仍占据压倒性优势,意大利思想家、科学家布鲁诺因宣扬“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那是1600年2月17日。由于长期存在的审查制度,1640年英国全年只印了可怜的22本书。弥尔顿生活的那个时代,能够合法从事出版业务的,只有极少数拿到政府执照的机构。英国《出版管制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能印行。”同时,那些被认为冒犯政府或宗教的著作要销毁,相关作者与出版商将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酷刑迫害。整个英国,似乎都在等待一声冲破黑暗的呐喊,来开全欧风气之先。
颇为诡谲的是,这篇振聋发聩的《论出版自由》,其实只是弥尔顿第一段动荡婚姻的副产品。1643年,弥尔顿与年仅17岁的玛利·普威尔结婚,这是他替父亲去乡下收租时所带回来的妻子。然而,结婚一个月后,新婚妻子提出要回娘家一趟。好巧不巧,此时英国内战爆发。悲剧的是,两家人分属议会派和保皇党两大阵营,结果就是两人长期的异地分隔。于是,饱受婚姻困扰的弥尔顿又开始了“小册子”创作,这一次他要为“离婚自由”辩护。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会里,法律只认可一种离婚,那就是一方犯下了通奸罪,其他任何理由的离婚都是不被允许的。在此,弥尔顿首次将性格相合、精神层面的兼容,提到了婚姻存续的最高决定因素,以此主张更加宽容的离婚自由。
正当踌躇满志的弥尔顿拿着自己的战斗檄文准备出版时,又是好巧不巧,新的出版执照令刚好颁布——新一轮更加严格的出版审查机制正式启动。毫无悬念,这篇离婚自由的辩护文成了审查制度的炮灰。于是,忍无可忍的弥尔顿再次抄起鹅毛笔,立马投身到新的小册子的写作中——这本小册子正是《论出版自由》。冒天下之大不韪,弥尔顿在文中强烈抨击了英国的审查制度。更离谱的是,他还将这本非法出版物带到国会会场上高调派发,向国会大声疾呼:“出版自由是一种人权!”所幸的是,贵为英国国会议员的弥尔顿并没有因这个疯狂之举而锒铛入狱。
博览群书的弥尔顿考察历史后,发现古希腊和罗马从来没有过“出版许可”这回事,基督教也并不排斥异端书籍。最早禁止异端书籍的是教皇马丁五世(1369-1431),此前英国从没有这种规定,因此《出版管制法》纯粹是近代的产物——它以宗教为借口,但恰恰是反宗教的。弥尔顿认为,出版许可制不仅会阻挠真理的传播,也会扼杀人的理性和尊严。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在此,弥尔顿祭出了一行掷地有声的金句:“一本好书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起来,是为着未来的生命。”如今,这句话就刻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阅览室的入口处。

纽约公共图书馆主阅览室的入口处刻着弥尔顿的格言
极为讽刺的是,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列举的限制出版的种种害处,却在遥远的大兴文字狱的满清王朝身上一一应验了。窃以为,鸦片战争的一部分答案,或许就藏在200年前弥尔顿这本不起眼的小册子里。
历史的回响
弥尔顿为人类的种种自由抗争和战斗了一生,却至死也没有看到《论出版自由》中的思想在英国实现(1674年弥尔顿逝世时,距离作品的诞生已过去整整三十年)。即使在《出版管制法》于1695年被废除后,《论出版自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著名新闻传播学著作《传媒的四种理论》(1956)中指出,《论出版自由》对与弥尔顿同时代的作者“影响甚微”,它“没有得到那个时代的多数作者和公众人物的重视”。然而,任何思想和观念的进化以及对制度的重塑都是缓慢的,真正的经典乃是一种缓慢而持久的思想力量,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世界的面貌和历史的进程。即使是那些长期被人遗忘的沧海遗珠,也总会有重现江湖的耀世时刻。
一个多世纪后,这部默默无闻的作品开始迎来了它的华丽转身,不断成为人们争相引据的文献。1778年,《论出版自由》第一次再版,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法国《人权宣言》(1789)接受了当年弥尔顿向英国国会呼吁的“出版自由是一种人权”的重要思想,认为“无拘束地表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两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1791),其中第一修正案这样写道:“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弥尔顿在书中提出的“观念的自由市场”和“真理的自我修正”,早已成为现代言论自由的基石。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地球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把出版和言论自由写进宪法中,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基本共识。
更重要的是,弥尔顿启发了身后的约翰·洛克(1632-1704)以及两百年后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等众多思想家。尤其是密尔,他在《论自由》(1859)一书中发展了思想市场理论。他认为,如果被压制的意见是正确的意见,人们自然就失去了修正错误、获得真理的机会;而即使被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意见,人们也就因此失去机会,从真理与错误的比较和讨论中,获得对真理更为清楚的认识和更加深切的信服。再者,通常情况下,现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完全正确,总有某些不足,而错误的意见中,也会包含着部分真理,只有借助与敌对意见的冲突和辩驳,才能使现有的真理不断补足、不断完善。
197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一篇名为《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论文中,逐字逐句地引用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的文字:“我们不能想象,将地球上的所有知识做成商品,像细毛制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样做上标记,发放许可证……”2011年,101岁高龄的科斯在《财经》年会致辞中再次强调:“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也许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压抑思想市场只会遭致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能够培育宽容,这正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这是弥尔顿自由思想在当代世界最珍贵的历史性回响。
当然,随着对弥尔顿、密尔等人自由思想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言论自由并非绝对,为了保证公共治安与普遍福利,某些言论必须受到限制。事实上,从操作性层面看,依法禁止某种言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禁止者不给出明确的认定标准,而是想禁止什么言论,就将之贴上某种负面且含混的标签。长期以来,许多文学作品因为被贴上“淫秽”的标签,被各国政府随意禁止出版。直到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淫秽”的三大标准确立后,政府再也不能以某本书涉黄为由,将其打入冷宫。由此,《包法利夫人》(1857)、《尤利西斯》(1922)、《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南回归线》(1939)、《洛丽塔》(1955)等一大批传统禁书,终于得见天日。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关于言论自由的研究,对司法审判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中,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的论断,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靠更多言论矫正异议,而非强制他人噤声沉默”的名言,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在弥尔顿看来,世上本无绝对真理,只有让不同意见争执冲突,彼此互补,部分真理才有发展为完全真理的可能。凡此种种,在《论出版自由》中都有精彩论述,并最终转化为“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Abrams v. United States, 1919)、“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Whitney v. California, 1927)等著名案件中的判词。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