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按:“正面连接”的报道《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日前引发广泛关注,也再次激起了关于“儿童之恶”话题的讨论。那些孩子为什么会亲手领着他们的“朋友”走上被侵犯、被强奸的道路,他们自己又遭遇了什么?近几年来,每每有残酷的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伤人甚至杀人事件发生,类似的话题一再被提起。是今天的孩子变得更道德败坏了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才能规避这一切,孩子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或怎样的惩罚?而因伦理和隐私方面的复杂考量,对这些恶性事件背后真实的儿童困境的分析往往浮于表面,这不仅无益于困境的解决和儿童的福祉,也加剧了成人对儿童心灵的误解和偏见。
我们都曾是儿童。从童年到成年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过程?对儿童来说,那些成年人难以理解的游戏仅仅是一种消遣吗?儿童世界的暴力与创伤归根结底是成人世界造成的吗?成人又应该怎样看待所谓“童真”呢?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Andrés Barba)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抛出的就是这些问题。
巴尔瓦的小说展现了神秘的、野蛮的甚至骇人的儿童世界,颠覆着成年人对纯真童年的扁平幻想,也挑战着现代人未经审视的生活态度。在《光明共和国》里,小镇褪下平静的表象,森林中的孩子们来路不明、行踪诡秘、持刀杀人,社会规范和道德秩序逐渐崩塌;在《小手》里,小女孩在孤儿院被杀死,而她们只是在实践着属于自己的“爱的游戏”。这两部小说向成人读者抛出了尖锐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无法接纳、拒绝承认甚至是忌惮恐惧于儿童的天性,身处其中的人是否都应为此负责?

巴尔瓦的创作几乎总是概念先行的,对语言哲学的敏锐洞察与他的现实关注密切交织,于是有了一个个乌托邦的又或者是反乌托邦的世界。从这一点看,他的写作同时有着很强的行动性,在儿童文学里创造游戏的花园,给予孩子真正的玩乐时光,在政治寓言和奇幻叙事中缔结承担的、反思性的思想主体。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新的语言,就无法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01 儿童的暴力令人震惊,因其动摇了成人对童年的美好幻想
界面文化:你的许多小说都深入探讨了儿童的精神世界。此外,你还创作了4部儿童文学作品。你为什么如此关注儿童群体及童年主题?
巴尔瓦:童年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史上都是一个母题。童年凝聚了社会所定义的童真、纯洁的力量,吸引着成人的关注,也会引发社会的情绪。不仅是童年的概念本身,社会文化对童年的整体情绪和态度也值得关注。
西方社会文化对儿童和童年的态度总是自相矛盾。一方面,童年被视为如天堂般没有义务或规则、只有纯粹的快乐与本能的阶段,成年人对此羡慕不已;另一方面,成年人又恐惧童年,因为孩子们是如此纯真且富有能量,我们难以真正洞悉他们的内心。
界面文化:你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童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非自然的产物,“童年是快乐无忧的”这种看法也是非常现代的。这让我想到尼尔·波兹曼的著作《童年的消逝》,他认为印刷技术普及导致知识的口语传播形式被文字读写取代,“童年”就产生于这种人为的文化鸿沟中。你认为当下社会对“童年”的看法是否存在着类似的鸿沟或误判?你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是以成人的视角还是以儿童的视角来创作的呢?
巴尔瓦:社会创建了教育体系和各类机构,期望尽早将他们培养成公民和成年人,童年与成人之间的文化鸿沟也就被人为地消除了。当某件事物像这样引发两种迥异的社会心理,一边羡慕一边恐惧,就说明我们无法与其中蕴含的能量和谐共处,这尤其体现在童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
另外一个我很关注的元素是暴力——不是成人对儿童的暴力,而是发生在儿童之间的暴力。实际上,暴力似乎也是童年阶段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我们为童年构建了一种如天堂般的幻想,认为那是不可触碰的幸福与纯真。看到孩子们表现出眼神、肢体上的冲突行为时,我们往往感到震惊和紧张,因为这动摇了成人对童年的美好幻想。当然,我在想象儿童之间的暴力和交往过程时,因为没有办法真正走进它,本质上也是一种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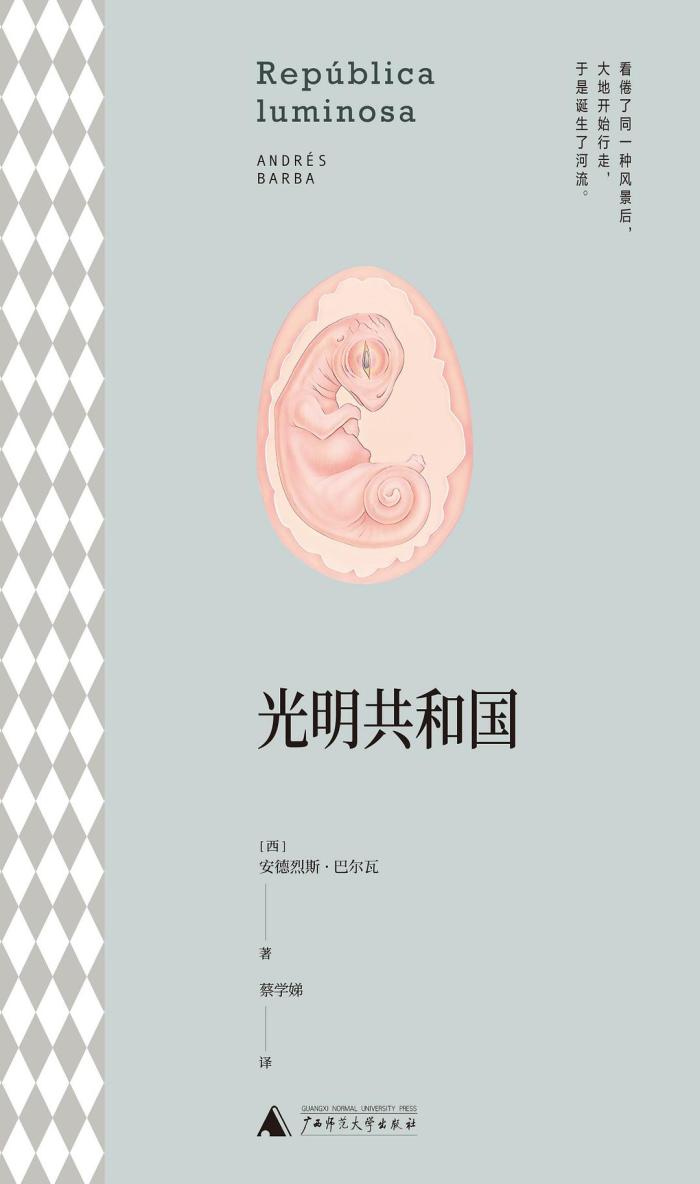
[西] 安德烈斯·巴尔瓦 著 蔡学娣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4
界面文化:在《光明共和国》《小手》《消磨》里写到的童年暴力和创伤元素,是你创作儿童文学时会规避的吗?还是说,你会将这些元素以某种变形融入到儿童文学写作中?
巴尔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每个创作者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创作儿童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教化?这两种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如果将儿童文学纯粹视为娱乐,它的教化功能就被削弱了。
这也与另一个问题相关联:我们应该告诉儿童什么?是否应该帮助他们理解这个世界?我们是为儿童提供工具,使之有能力理解和应对世界,还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理解世界?
我想举个例子,我写的第一本书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在一个小村庄里,天上的星星突然暗灭了。村里的智者说,其实星星并没有消失,天空中有一个开关,只要搭起梯子爬到最高处打开开关,就能重新点亮星星。于是众人把家里的梯子贡献出来,想共同建造一个长梯。但有一位老人拒绝为集体做贡献,他说星星亮不亮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后来当一个孩子和他建立了私人的友谊,他就愿意把梯子以个人名义借给这个孩子,如此,村里人实现了集体的愿望。对这位老人来说,个人之间的爱是超越了共同体的爱的。当我把这本书给一位西班牙的儿童文学编辑时,她不认同我撰写的这个结局,认为共同体的利益应当是高于个人的。这就引发了一个教育理念上的冲突: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们重视怎样的价值观?是以真理为导向,还是以道德为导向?这样的冲突在创作儿童文学时是常常会遇到的。
界面文化:西方社会文化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个人价值优先于集体价值。在这个例子中却反过来了。
巴尔瓦:是的,这确实很少见。但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者的个人信念与想给儿童呈现的“应然”世界之间的冲突。创作者有着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但他们认为孩子应该学习的观念可能与此不同。
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代表作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影响了我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对儿童文学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让孩子们感到兴奋和愉悦。儿童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快乐,如果阅读本身不能带给他们快乐,他们永远不会主动接触文学,只会在家长或学校的要求和逼迫中读书。我想创造一个令人快乐的花园,邀请孩子们过来玩一玩,就是我写儿童文学的最大原则。
02 游戏于成年人是消遣,于儿童则是一种生命形式
界面文化:小说《小手》取材于真实故事。在新闻报道中这类故事通常会被描述得很恐怖,但你却书写了儿童群体内部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将游戏中的暴力和真正的暴力区分开了。小女孩玛丽娜受到了其他女孩的暴力对待,但在她发明的洋娃娃游戏里,是她教大家表达对彼此的爱。“游戏”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你认为“游戏”能治愈“暴力”吗?
巴尔瓦:这个故事源自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Clarice Lispector,代表作有《星辰时刻》等)的作品,这是作家的女仆分享的亲身经历。女仆曾在孤儿院生活,她们中的一个女孩死去了,其他女孩把尸体当成洋娃娃“玩耍”了一个礼拜。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初听时我感到一种复合性的恐惧与惊奇,无法确定这种感受是恐惧还是迷恋。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对这个故事的恐惧正是来源于成人视角,而对它的迷恋则来源于孩子的视角。从成人世界来看,这是一种令人想要规避的野蛮和暴力。但在儿童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一则关于“爱的游戏”的故事。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要元素。一是“失乐园”,那些女孩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孤儿院中,玛丽娜这个新来的孩子就像是来自新世界的使者,会在孤儿院这个旧世界引发对比、冲突、悲伤,但也会激发新的事件。

[西] 安德烈斯·巴尔瓦 著 童亚星 刘润秋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4
第二是游戏,儿童和成人对游戏的态度是不同的。成人玩游戏通常是为了消遣时间,他们往往也认为儿童的游戏只是“弄着玩儿”。然而,儿童对游戏是非常较真的,这不啻为一种生命形式,他们在游戏中投入了全部的心力,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体验生与死,儿童把这些体验带到了游戏中,所以在游戏中才会出现杀人或死亡,对他们来说游戏是生死攸关的。因此,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是极其严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儿童那里学习游戏的真正意义,重新看待游戏和我们的生命。
界面文化:“失乐园”这个概念非常有趣,它是否根植于《圣经》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几乎不会把孤儿院与“失乐园”联系起来。
巴尔瓦:“失乐园”是指《圣经》里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所在。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禁果被迫离开天堂的时刻,也是他们意识的开端,完全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就此结束,他们开始体验人间疾苦。对我来说,天堂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圆形结构。在这个“圆”之中,我们无需在自身与他人之间反复比较,也就更为幸福。
我觉得现代人使用社交软件也是一个不幸福的来源,因为总是会拿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比较,所以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失乐园”。当一个封闭的“圆”被打开,天堂就结束了。因此,在西方文化中,离开天堂意味着意识的开始和天堂的结束。

界面文化:除了创作小说,你也是一位多产的翻译者。语言和哲学的学术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比如在《光明共和国》中,32个孩子自创了一种新语言,你写到,孩子们的出发点似乎“完全是游戏和创造的冲动”,而非“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理论”,这看起来就好像含有你对自己所学的一种“反叛”和反思。
巴尔瓦:哲学和语言学的学习经历确实对我的写作生涯有很深的影响。我的创作几乎总是“概念先行”的,或者说以概念为导向,而非简单地构思一个故事。有些作者更关注叙事或情节的发展,而我不论是写小说还是随笔,通常都源于一种哲学上的疑问,想要探讨一些概念和想法。
例如,我构思《光明共和国》时主要思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童真?第二,如何看待社会或集体的共罪及其应负的责任?在这部小说中,政府的追捕使孩子们全部丧命,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种集体性的罪责,是接受认领这份罪责还是否认它?
抛开这本书的内容来看书名,“光明共和国”本身就是儿童想要创造的一个新世界,也可以说是天堂或乌托邦。在创造天堂时首先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所有的乌托邦都需要语言的发明。比如,一对恋人相爱时往往会为对方取一个独创的小名,在此之前恋人从未被这样称呼过,这就是创造新语言的一种体现。我们在创造新的语言和词汇时,也在以某种方式重新定义现实,现实和语言之间是双向的互动,这就是小说里这群孩子们通过发明语言来构建新社会的原因。没有新的语言,就无法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03 每个人都深切地渴望被爱,而儿童获得爱的渠道闭塞又狭窄
界面文化:我在你的作品中确实发现了许多乌托邦式的概念。例如在《消磨》中,当女孩进入青春期,她对自己的身体变化非常敏感,生活琐事也越来越令她难以忍受,于是她逃到了公园里。公园可能就是她的一个乌托邦,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空间。之后,她又因为拒绝进食被关进了一个治疗厌食症的封闭式诊所。
巴尔瓦:我写这个故事时最关心的就是厌食症这个现象。从病理学角度来看,厌食症是一种有害健康的、需要介入治疗的疾病。但从哲学角度来看,厌食症的体验类似于苦行,是对纯净和神性的追求和对动物性的剔除,例如拒绝进食或者吃素,这些行为都是对世俗世界的否认,厌食症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宗教性的审美追求。
因此,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概念:首先,什么是正常?厌食一定是一种疾病吗?那么与之相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健康呢?其次,我们是否应该保护那些想要自我毁灭的人?自我毁灭是否也能够成为人面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在这个关于厌食症的故事中,标题“消磨”并不单单指厌食症对女孩体重与体型的消耗,也指向女孩在家庭和诊所中体验到的爱。女孩通过厌食症为自己建立了一个自我隔离的坚固结构,诊所里结识的朋友给予她爱和陪伴,打破了厌食症的隔离。但是,无论是家庭里的亲情,还是在诊所建立的友谊,这些爱的关系总是极其脆弱的,最后都慢慢地消磨掉了。
界面文化:最近有一篇报道讲述了一个11岁的中国女孩的故事。她在接受义务制教育时成绩不好,父母在学校的劝退下让她辍学。女孩的父母忙于生意疏于照料她,她被关在家里更加身心孤独,于是通过互联网结交到了一群处境相似的朋友,这个小圈子却又把她带进被暴力、被性侵和被迫卖淫的深渊。女孩的悲剧是多方面的,缺乏爱和陪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巴尔瓦:这是一个悲剧。不论是这个事件里女孩遭遇的暴力,还是其他类似的令人感到恐怖的儿童事件,它的恐怖性就在于儿童获得爱的现实渠道是如此闭塞和狭窄,以至于愿意通过如此令人绝望的方式得到哪怕是一点点“爱”。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深切地渴望被爱——不是狭义上的男女之爱,而是广义上的交流和关爱,在所有由人类造成的痛苦中,都深藏着对爱的渴望。因此,我们更应该对这些儿童给予同情和关注,而非不解甚至鄙视。
界面文化:《消磨》是《正当意图》这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正当意图》的四则故事《血缘》《消磨》《夜曲》《马拉松》代表着什么,“正当意图”这个词指的是什么?
巴尔瓦:读者可能会发现,在《正当意图》的四个故事里,每个主人公都有些病态,各自胶着地处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将自己的全部意志、愿望或爱投诸单一的点。比如说《马拉松》里男主角就把生活的精力和关注点都放在跑马拉松上,《消磨》里的女孩也是这样,她全心全意地用厌食来对抗世界,将厌食作为一个正当意图来坚守,即便在家人看来她这么做毫无必要。
这样的形象似乎同时具有愚蠢、执着、神性的特点,就像圣人和愚人也是相似的,他们都把自己的执念置于生活的最中心,一切都围绕其打转。所以,我在小说中非常关注事物辨证矛盾的两端,会书写事物之间相反又相似的特性——就像厌食症一样,它是一种确凿的疾病,但同时也包含着彻底的解放的一面。
04 疫情让很多人经历了幽灵般的生活
界面文化:你在2023年的新作品《前世的最后一天》(El último día de la vida anterior),里讲了一个关于“鬼魂”的故事,这和你以往的虚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能聊聊你构思这个故事的动因吗?
巴尔瓦:《前世的最后一天》目前还没有在中文世界出版,这部作品的创作源于一种特别的图像感受。我写每本书的动因都不同,有些书源于概念性的构思,比如我写《光明共和国》是想创作一部政治寓言。《前世的最后一天》的灵感则源于一幅图像,它也和我写作的母题有关:在一座房子里,一位女性通过房间内的镜子看着她自己。我想象她通过房间的镜子能看到自己前一天所做的事情,她日复一日地进入这座房子去观看前一天的自己,并为后一天的自己预设前一天的行为“脚本”。我们通常无法从外部看自己,所以,偶尔在录影中或者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我们会有一种新奇的、陌生化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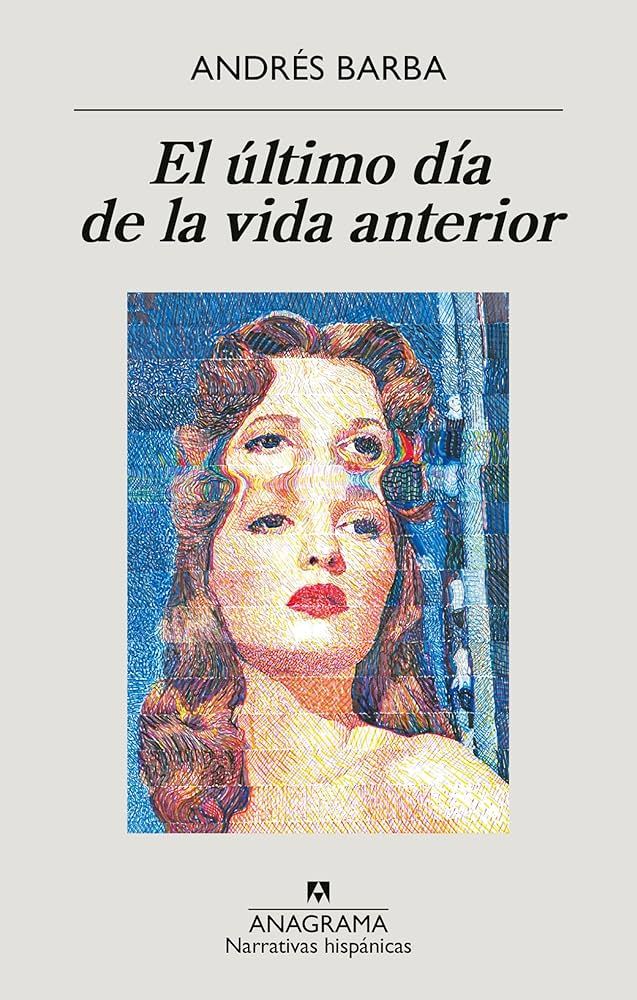
疫情期间,这种感受变得尤为强烈。大家都被困在家中,仿佛成了自己生活的幽灵。我们的真实生活仿佛在外面发生,而我们自己则如同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们常常无法认出自己是谁,这种隔离的、停滞的、不真实的感觉与书中那位女性的经历相似。因此,我觉得这幅图像和疫情期间的共同体验非常契合,疫情让很多人都经历了这种幽灵般的生活。
界面文化:“鬼魂叙事”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拉丁美洲文学中不乏类似的讲述方式,这和你的写作是否有内在关联?
巴尔瓦:一方面,我的创作受到英语文学的影响,英语文学中也不乏鬼魂叙事的传统。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两位英语作家是狄更斯和亨利·詹姆斯,尤其是后者。所有写出伟大的鬼魂故事的作家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作家,现实主义和鬼魂叙事在某种程度上紧密相连。鬼魂故事要讲得有效,就必须非常真实,内部必须有很强的现实逻辑性。
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受到拉美文学的影响,尤其是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文学,即拉美文学里靠近阿根廷、乌拉圭这一区域的文学,以博尔赫斯为代表人物。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阿根廷记者、小说家、翻译家)曾编纂过一本幻想文学故事集,幻想文学几乎成为了拉丁美洲文学的标志。
拉美文学中的鬼魂叙事与英语文学有所不同。如果说英语文学常常严格区分鬼魂世界和正常的生活世界,二者之间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鬼魂被视为现实中的“异物”,那么拉美文学中的鬼魂世界和活人世界是平行的,死者的鬼魂能与生者共存,且被视为现实的自然延伸。这和东方文化对鬼魂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界面文化:中国文化中确实有着丰富的鬼魂和灵异故事的传统,鬼魂被视为现实的一部分,有时它与一些灾难或困境相关联,民间相信这些灵异现象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或引发不幸。我们也会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鬼魂的存在,比如说你做了背德之事,鬼魂就会扮演惩戒的角色;而如果你做了好事,鬼魂则会保护你。
巴尔瓦:据我所知,中国人是有祖先崇拜的,会相信自己的生命与祖先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联系,因此鬼魂具有如神明一般的保护性力量。在西方不太一样,鬼魂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威胁的、有敌意的存在。在拉丁美洲的文学传统中,鬼魂和现实世界边界更模糊。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这本书可以说是20世纪西班牙语文学中最杰出的鬼魂小说之一。书中生者和死者的界线完全模糊,读者读完后也无法分辨谁是活人、谁是死人,这种模糊性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 著 屠孟超 译
译林出版社 2021-1
你提到中国文化里鬼魂的预言和道德规训作用,西方也是如此。一个常见的叙事动机是某人由于生前未能解决某件事情,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斩断,因此鬼魂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半生半死”状态,需要通过和活人之间形成互助的契约或承诺来完成未竟之事,以便完全进入死亡的世界。因此,西方的鬼故事往往也是道德寓言。
界面文化:今年你获得了阿根廷国籍,是什么让你决定申请阿根廷的公民身份?我们知道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你如何看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呢?
巴尔瓦:15年前我就和一位阿根廷女子结为夫妻,这10多年里,我都不在西班牙而是在阿根廷生活,我的孩子也出生在阿根廷。拥有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双重国籍并非意味着对西班牙国籍的否认,反而公民身份的转换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解脱、或者说拓宽和延展的感受。
我和阿根廷的关系,不仅仅是与我的妻儿的私人关联,更是与阿根廷所在的整个拉丁美洲的联系。我对拉美文化是如此熟悉,它仿佛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同时,我感到自己像是摆脱了对身为“西班牙人”的认同,也跳脱出了一种流行的、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病症,因为它往往伴随着对其他文化的贬低。如果我们不去拓宽自己的视野,主动了解其他国度的文化,也无法成为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者。因此,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愈。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